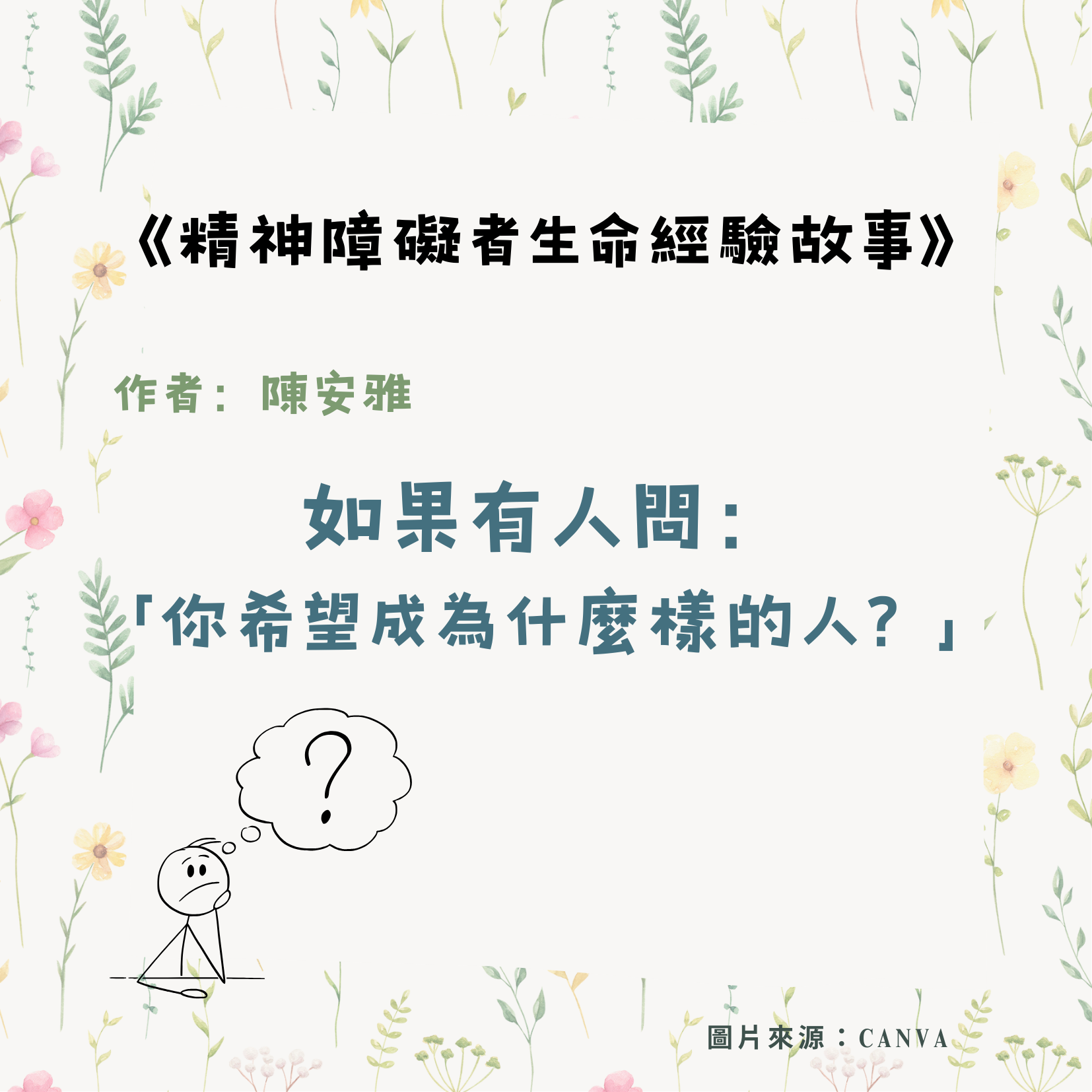作者:陳安雅
我是精神障礙者,一直努力融入社會,卻一次次被環境擊倒,大學四年級重度憂鬱症發病,拖了半年才進入治療,過了一年才完全緩解,也進入第一份工作,但職場壓力讓我完全耗竭,最後辭職,甚至一度想自殺。之後求職不順,擔心抗壓性太低,最終失業了一陣子,也領取了政府的失業補助。我想說的是,精神障礙者不是不想工作,而是缺乏適合的支持系統來幫助我們穩定就業。即便是相對高功能精障者,仍然難以穩定就業。
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在NPO,這是一個相對友善的環境,但我仍因為疾病時常請假,剛好又遇到家人過世,導致身心再度崩潰。我的主管是個非常理解的人,他願意彈性調整我的工作模式,但他也常常陷入兩難:「要以人為本,還是要完成組織的任務?」我想說的是,現有的就業環境,即使遇到友善的主管,仍然沒有完善的支持系統來讓精神障礙者穩定發揮工作能力。
這些年來,我的答案一直在變動。曾經,我以為自己只要努力適應社會,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,就能過上「正常的生活」。但後來我才發現,對於精神障礙者來說,這條路並不只是努力就能走得順暢。我們需要的,不僅僅是機會,而是一個真正適合我們的環境,一條能夠讓我們穩定發展、發揮自身價值的職涯道路,對我來說總是有個困惑,為什麼社會總是創建一個環境,然後希望所有人去適應那個環境,而不是因應人們創建任何人都適合生存的環境呢?
從被照顧者到助人者的轉變
回顧自己的經歷,憂鬱症發病後,我嘗試回到職場,卻在一次次的碰撞中耗盡力氣。即使找到一個相對友善的環境,還是因為疾病而難以長期穩定工作。在那些低潮反覆住院的時刻,不是護理師讓我離開病房去參加OT課程,而是病友陪伴我從起身開始、慢慢在病房走動、慢慢的去上課,這些人對我的陪伴,讓我重新看見希望——不是以專業輔導者的身份,而是以「同樣走過來的人」的視角,告訴我:「我懂你」、「我知道妳躺著不是很懶,而是真的起不來」,“同理” 跟 “共感” 終究是兩個不同的事情。
這種支持,讓我開始思考:如果我曾經被這樣的力量扶起來,那麼,我是否也能成為別人的支撐?於是,我選擇回到大學讀社工系,試圖用專業知識讓自己有更穩定的助人能力。但內心仍然不時浮現疑問:「我真的能夠勝任嗎?我還是個需要被幫助的人,真的能去幫助別人嗎?」這個問題,我想,並不是只有我有過。許多精神障礙者,即便願意投入助人工作,也常常會有這樣的自我懷疑。但後來,我才理解:「助人者」與「受助者」從來就不是絕對對立的身份,而是一條流動的光譜,有時我們需要被支持,有時我們有能力支持他人。
期待讓這條路更清晰、更穩固
我期待,台灣能夠真正為精神障礙者提供一條清晰的職業路徑,而不是僅僅停留在「服務方案」的概念裡,如今卻在就業路途上困難重重。我期待,未來的精神障礙者不再需要為了找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而四處碰壁,而是能夠走上一條既發揮自身經驗、又能獲得穩定支持的職業道路。我期待,當我們談論「復元」時,不只是指個人的心理狀態,而是指「社會是否提供了一個讓我們能夠發揮價值的機會」。當精神障礙者能夠成為助人者,這代表的是:「我們不再只是被照顧的對象,而是能夠貢獻社會的一份子。」
我想助人,但沒有合適的職業路徑,如果當時……
我們不只是需要被支持的人,我們也能成為支持他人的人。
我們不只是社會需要照顧的對象,我們也能成為社會的一部分。
有時我會想,如果台灣有穩定的「同儕支持員」職涯發展,我或許不需要花四年重新回到學校,只是為了尋找一條適合自己的職業路徑。或許,我不會在求職的過程中一次次碰壁,不會因為找不到穩定的工作而懷疑自己的價值。或許,那些跟我有類似經歷的人,不需要像我一樣走那麼多彎路,而是能夠更早地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職涯發展方向。這也是我為什麼對「同儕支持員」充滿期待——不只是為了自己,而是為了更多和我一樣,在復元路上努力走著的人。我期待這一天的到來,也期待這條路能夠真正被走出來,走得長遠,走得穩固。
這個改變的不只是個人,而是整個社會
這不只是關於個人就業,而是關於社會如何看待精神障礙者的價值。當我們能夠在一個穩定的支持系統下發展職涯,這不只是減少失業率的數據,而是讓更多人有機會透過這份工作,重新找回自己的意義與價值。
這樣的改變,對政府來說,是一項能夠減少長期醫療支出、降低失業補助的投資;對企業來說,是一種提升職場多元性與包容性的機會;對社會來說,則是一種讓精神健康議題更加可見,並且真正落實「復元」概念的重要步驟。
而對於精神障礙者來說,這是一個從「被照顧者」轉變為「助人者」的機會,讓我們不只是活著,而是能夠活出自己的價值。